《病床边的陌生人》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病床边需要“陌生人”,但理想和现实的步调并不一致,“陌生人”走到病床边的过程并不顺利,而是经历了各种纷争和阻碍。第二部分,咱们就来还原这段历史,看“陌生人”是怎样一步步走进实验室、走到病床边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二战后的美国医学界延续了战争时期的做法,医学家们不仅认为自己的做法目的高尚,不存在伦理问题,还把医学看成是自留地,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自主裁量权,外部人士无权对自己的专业判断说三道四。面对这种傲慢的态度,必须有人站出来加以改变。书中写到,1966年,美国哈佛医学院麻醉学教授亨利·比彻成为医学界的“吹哨人”,他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22个案例揭露了美国二战后人体试验中普遍存在的医生滥用权力的现象。作为一线医生,比彻早就看遍了人体试验中的种种伦理污点,他认为,道德上的瑕疵会让医学的名誉蒙尘,所以,伦理合法性对医学来说至关重要。而他做出改变的方式,就是通过文章向公众揭露医学的黑暗面。比彻文章中的案例个个触目惊心,稍微举几个例子,你就能感受到。比如,纽约大学儿科学系主任索尔·克鲁格曼博士,为了确定感染性肝炎的易感期,特意在一家收容智力缺陷儿童的学校里进行试验,诱导很多儿童感染肝炎。又比如,康奈尔大学内科学副教授切斯特·索瑟姆博士,为了验证人体对癌症的免疫机制,向22名年老体弱、神志不清的患者体内注射了活性肝癌细胞,他只告诉这些受试者会给他们注射一些细胞,没告诉他们注射的是活性癌细胞。再比如,NIH心脏病学研究员尤金·布朗沃尔德博士,为了研究人的心脏生理学反应,在完全不了解潜在危害的情况下,把一个水银张力计缝合在试验对象的左心室表面,同时,对受试者的两个心室插管。 面对这些令人震惊的案例,社会各界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医学界对比彻的文章不以为然,有人说,比彻举的例子只是个别情况,不能代表大多数;还有人认为,为了科学进步,牺牲社会边缘群体的权利是合理的。但医学界以外的社会公众反应极大,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医学进步的背后,竟然隐藏了如此不堪的黑暗面。社会舆论一经兴起,各方面的压力就随之而来。为了避免负面影响扩大化,NIH开始主动调整政策,颁布了一项关于人体试验科研项目的指导方针,通过设立一个机构审查委员会,让医学同行之间对人体试验等行为互相评议和监督。然而,这个委员会并没有邀请医学领域以外的人参与决策,所以,本质上它还是医学界的内部游戏,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大名鼎鼎的FDA,迈出的步子明显更大。书里写到,1966年,FDA决定,将医学研究分为治疗性和非治疗性两大类,并立即禁止一切没有经过受试者同意的非治疗性研究;而且,就算是治疗性的研究,也必须在患者同意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虽然医学界对这类监管不情不愿,但FDA的监管规则还是标志着科研人员和受试者之间的权力制衡进入了新阶段,单凭“人体试验必须事先征得受试者同意”这一条,就能消灭比彻列出来的大部分案例。从这一刻起,医学界再也不是医生们的“一言堂”,社会各界的声音和监督开始涌入这一领域,“陌生人”终于走进了实验室。那么,至此“陌生人”对医学的监督就达到目的了吗?远远没有。因为这时,“陌生人”的监督还没有深入到医院的病床旁。FDA的监管规则只适用于医学研究,日常的临床诊疗活动并没有受到限制,而且,习惯于自己制定规则的医生,也丝毫不愿意让他人干预自己的工作。让“陌生人”在病床边占据一席之地,就相当于把实验室的新规则扩散到病房里,这显然会削弱医生的权威,降低社会对医生群体的信任程度,医生肯定是不乐意的。刚刚我们提到,在二战后,医生的临床治疗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来医生都是上门看病,虽然医疗手段落后,但医患关系比较融洽。二战后,随着各种专业仪器陆续问世,医学学科不断细分,就诊效率不断提高,诊疗活动发生的地点,逐渐从病人的家里转移到医院。冷冰冰的仪器、指标、数据,代替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嘘寒问暖。相应地,医生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他们的群体形象也逐渐褪去了温情的一面。普罗大众对医生们越来越不满,针对医生的医疗诉讼越来越多,社会开始呼吁变革。书中指出,在压力之下,美国医院协会在1972年通过了《患者权利法案》,这个法案第一次明确,医院里的治疗和试验活动,要首先取得患者的同意。虽然这个法案缺少强制和惩罚程序,但仍然意义重大,因为它标志着医生开始与患者分享权力,为“陌生人”走进病房打下了基础。接下来,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更进一步,让“陌生人”走到病床边,不仅有了合理性,还有了必要性。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就有移植器官的愿望,但直到上世纪50年代,器官移植才真正实践成功,最开始是肾脏移植技术,之后是心脏等其他器官移植技术。器官移植技术虽然意义重大,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供体永远是稀缺的,这样一来,由谁来决定器官的分配就成了最核心的问题。肾脏移植专家可能精通于移植技术,但他们显然没有资格独自决定器官的去向。而且,在对器官的需求面前,每个健康的人都成了潜在的器官供体。医学原来的目的是治愈生病的人,但现在可能伤害到健康的人,这就为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难题。所以,病床边的监管同样势在必行。美国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首先站了出来,他从1968年就开始呼吁,要成立一个卫生科学和社会委员会,专门负责评估和报告生物医学发展的伦理、法律、社会和政治影响,并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专业医生们在面对可能到来的约束时,意见自然是一边倒地反对。绝大多数医生都认为,让大量非专业人士提出约束医学职业的建议,会阻碍医学的进步,还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明尼苏达大学医院外科主任欧文表示,“专业的事最好交给专业的人……我不觉得神学家、法学家、哲学家或其他什么人能在医学方面提供什么帮助。”医学科研人员的看法类似,在他们看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资助他们研究,然后靠边站就行。” 但在非专业人士和比彻这些非典型医生看来,公众以各种方式参与塑造医学发展是天经地义的。比彻在听证会上说:“科学不是碾压其他一切价值的最高价值,它必须在价值序列中排队。”哈佛大学科学史专家门德尔松也表示,“在社会要素方面,医生的判断……不比非专业人士更高明。”虽然两方的争论非常激烈,但呼吁监管的呼声最终还是压过了反对的声音。几经波折之后,1974年,美国政府最终成立了“国家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人体受试者保护委员会”,终结了医生在医学问题上“一言堂”的地位,让背景各不相同的“陌生人”,比如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法学家进入医学领域发表意见,进行监督,这标志着“陌生人”真正走进了病房,开始影响医学诊疗过程中的决策。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后来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几个案例,继续推动了更多的外部人进入医学领域,逐渐将医学界的决策机制塑造成今天的模样。我跟你分享一下最著名、意义最重大的“昆兰案”,它标志着“陌生人”向病床边持续数十年的进军达到顶峰。1975年,年仅22岁的少女卡伦·昆兰,因违规使用药物突然晕倒,从此陷入长期昏迷。当她的父母意识到她再也无法苏醒之后,便决定请医生拔除昆兰的呼吸辅助设备,让她安静地离去。但这一请求遭到医院方面的拒绝,因为医生们认为,从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说,昆兰还没有死去,所以他们不能停止治疗。得知消息的昆兰夫妇十分心痛,并决定上诉至法院,希望通过法律的判决让女儿获得解脱。最终,他们的请求获得州最高法院的支持,得以拔掉了女儿的呼吸机。 “昆兰案”的案情并不复杂,但为什么说它意义重大呢?因为这个案件的核心在于,医生认为自己的治疗决策出于专业判断,不应该受到法院等社会各界的干涉,如果今天法院的判决能影响昆兰的生死,那未来医生的一切行为就都可能受到法律无孔不入的制约。但法院的判决亮出了鲜明的态度,那就是决策权不能只掌握在医生手里。“昆兰案”的判决,从法律上改变了医学的权力结构,让“陌生人”进入医学决策变得有法可依。更进一步的是,由于民权运动频发,美国政府又成立了“总统医学和生物医学及行为研究伦理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研究的虽然是医学问题,却由律师和哲学家主导。在最初的11名委员中,只有3人是执业医师,其他都是传统意义上医学界以外的人士。委员会后来就很多议题展开了讨论,达成了很多重要成果:比如,医患关系应该坚持“共同参与、互相尊重、共享决策”,医生应该积极分享权力,而且,医疗救治的最终决定权应该属于患者,等等。经过几十年的博弈,“陌生人”终于走进了实验室,走进了医院,走到病床边,在社会各界的监督下,医学的发展也终于步入正轨,并从美国推而广之,深刻影响了全世界医学领域的伦理规范。今天,在来自不同领域的“陌生人”的注视下,就算是最有野心的科研人员,也不敢轻易进行原来那种存在严重伦理问题的人体试验,一旦铤而走险,就可能身败名裂。
《病床边的陌生人》3.第二部分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读书笔记 » 《病床边的陌生人》3.第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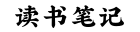 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评论前必须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