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边的陌生人》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好,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病床边需要“陌生人”?
医学发展至今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陌生人”走到病床边,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要弄清出现这种变化的真正原因,我们还得从二战前的医学发展史讲起。二战以前,医学研究者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式和今天大不相同,绝大多数医学试验都是在熟人社会中进行的。主导试验的往往是单枪匹马的医生,试验对象则大多是医生本人、他们的家人或邻居。而且,这些试验一般都带有治疗目的,只要试验获得成功,就能让试验对象本人直接受益。比如,书中讲到英国医生、现代免疫学之父爱德华·詹纳的故事,他为了找到让人体对天花免疫的方法,就先后在自己的儿子和邻居家的小男孩身上做了试验,最终发现,通过接种牛痘,可以让人对天花免疫。你看,这个试验就是典型的在熟人社会中进行的,小男孩的父母信任詹纳,所以,允许他在自己的儿子身上进行试验,同时詹纳也要为试验的结果负责,而且一旦试验成功,小男孩就能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这就是医学科研传统的开展方式。同理,传统的临床诊疗也是在熟人社会中进行的。过去,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医院,需要看病的话,人们就会让医生来家里出诊,一边拉拉家常,一边聊聊病情。虽然当时的医学技术比较落后,医生对绝大多数疾病都没什么辙,但医患关系总体上是很融洽的。这时候,医学领域很少有伦理上的问题,自然不需要外部的监督,也不需要“陌生人”的存在。然而,二战期间,情况开始有了变化。因为战争的刺激,医学进入快速发展期,青霉素等一大批新药开始迅速投入使用。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新的药品或者疗法在正式使用之前,肯定要先进行大量的人体试验。这时候,传统的那种小规模的、基于熟人之间信任的医学试验模式,已经没法再满足大规模的试验需求。更何况“是药三分毒”,仍处于研制过程中的新药,安全隐患尤其大,一般来说,没人会自愿充当试验的“小白鼠”。可是,医学需要向前发展,这该怎么办呢?答案既现实,又残酷。既然没多少人愿意主动参与,科研人员就开始寻找那些无法拒绝的试验对象。什么样的人无法拒绝呢?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就是那些社会中最弱势、最边缘的群体,比如监狱里的囚犯、失去家人的孤儿、养老院中的老人,以及医院里的精神病人。二战期间,以赢得战争为理由,在社会弱势群体身上进行医学试验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书中谈到,为了找到能治疗疟疾的特效药,美国医生阿尔夫·阿尔文故意让数百位精神病人和囚犯感染疟疾,试验期间虽然有被试者意外死亡,但根本没人在乎,试验进度也丝毫没有受影响。 今天,这种明目张胆侵害弱势群体的试验是无法想象的,但二战期间,为了赢得战争而牺牲弱势群体的行为,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因为在战争状态下,社会很容易形成一种共识,认为在战争面前,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国家做出贡献,年轻的士兵们在一线冲锋陷阵,生活在大后方的人也应该做出牺牲,比如,为医学试验献出自己的身体。如果说,战争时期,这种做法还算有一点冠冕堂皇的理由的话,那么,二战结束之后,这种侵害弱势群体利益甚至生命的做法仍然得以延续,就很难说得过去了,但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1945年二战结束,但美国医学界的主流认识是,未来战争随时有可能到来,所以绝不能放慢科研的步伐。况且,二战期间,医学在短短几年内的进步,就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总和,所以,科研人员普遍认为,他们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美国成立了国立卫生研究院,简称NIH。作者指出,在战后,这家机构承担起引领美国医学发展的责任,从它获得的预算我们就能看出,战后美国政府对医学研究的重视程度:1945年,NIH还只有70万美元的拨款;而到1955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3600万美元;1970年,则攀升至15亿美元。期间,凭借着强大的财力,NIH资助了大约11000个科研项目,其中有三分之一都涉及人体试验。 战后开展的这些科研项目,试验对象的待遇如何呢?以NIH下属医院开展的项目为例,虽然这家医院对患者和参与人体试验的志愿者保证,他们的个人福利会被放在第一位,但实际上,没有制定任何正式程序或机制来保护患者。说白了,NIH只是给患者和志愿者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能不能兑现全凭科研人员的自觉。那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的自觉水平如何呢?答案是并不怎么样,书中列举的很多案例都能证明这一点。比如,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美国一组科研人员为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特意选择了一批患有梅毒的黑人作为试验对象,对他们进行定期的身体检查,但不进行任何治疗。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可以治疗梅毒的青霉素明明已经问世,但科研人员仍然刻意不为这些黑人进行任何救治,放任他们饱受病痛折磨,目的就是为了做试验对比,检验药物的疗效。 再比如,为了探究避孕药对人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副作用,美国圣安东尼奥的一家诊所在1972年秘密开展了一项试验,把来诊所开避孕药的女性患者分成两组,一组开具避孕药,另一组开具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安慰剂。结果不难想象,获得安慰剂的那一组女性,有很多人意外怀孕。但毫不让人意外的是,这些女性患者都是墨西哥裔,和梅毒试验中的黑人一样,都属于美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这两个例子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战后美国医学界的常规操作。科研人员这么做,既是出于私心,也出于公心。一方面,试验获得的成果,可以帮他们获得教职和荣誉;另一方面,二战期间接受的实用主义教育也让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努力。没错,一切伟大的工作都有造福社会的终极目的,但问题是,好的目的就能弥补错误的方式带来的损失吗?二战期间,纳粹医生对集中营犯人实施的暴行殷鉴不远,美国医生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非自愿的人体试验,和纳粹医生之间的行为真的有本质区别吗?很明显,并没有。我们没有资格为了其他人可能的利益,去决定让另一个人承担受伤害的风险。承认这些非自愿医学试验的合法性,就相当于为是非颠倒的行为敞开大门。所以,医学领域的科研活动,应该而且必须受到监督。更进一步而言,不仅医学科研应该受到监督,临床诊疗也需要被纳入监督的范围。二战后,医学在临床诊疗方面遇到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已经超出了医学本身能够解决的范畴。比如,如果医疗资源有限,而等待救治的病人太多,那应该由谁来决定资源的分配?医生能做得了这个主吗?又比如,器官移植技术的发明,为很多器官衰竭患者带来了生存的希望,但器官供体的数量永远无法满足病人的需求,那么,该由谁决定器官的分配才最合理呢? 再比如,医生真的有权替病人做出所有的治疗决策吗?患有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是否应该得到治疗?永远无法苏醒的植物人,是否应该停止维持生命?在面对类似的艰难抉择时,治疗方案的最终决定权,到底应该掌握在医生,还是掌握在患者家属手里?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显然已经超过了医学的边界,如果医生们坚持把权力握在自己手里,势必会引发一轮又一轮的伦理道德风波。一切的变化都证明,不管是科研方面,还是临床诊疗方面,医学都不能再由医生们全权把持,引入社会各界的讨论和监督势在必行。所以,以,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法学家为代表的“陌生人”,需要走进医学实验室,走到医院的病床边,替全社会履行对医学监管的使命。
《病床边的陌生人》2.第一部分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读书笔记 » 《病床边的陌生人》2.第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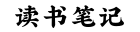 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评论前必须登录!
注册